发布日期:2025-02-16 22:07 点击次数: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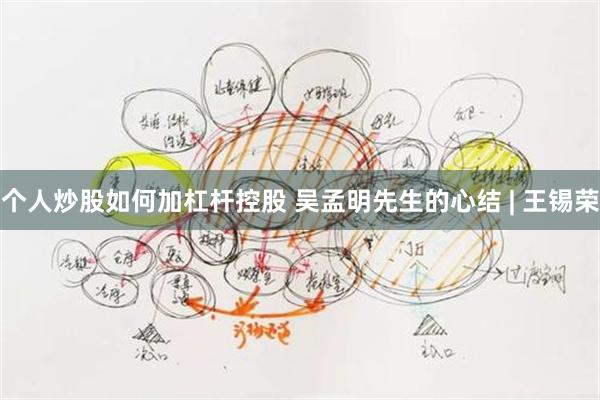
吴孟明先生是陈独秀的外甥孙子个人炒股如何加杠杆控股,他的祖母是陈独秀的大姐,嫁给富商吴向荣。吴孟明曾写过《我的舅祖父陈独秀》一文,回忆了他心目中的陈独秀,写得很是亲切感人。
2001年5月20日,我收到吴孟明先生的来信,信中谈到他舅祖父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但我跟吴孟明先生素不相识,此书与我也无干系,他为什么会写信给我呢?且来看看这封短信:
尊敬的王锡荣馆长:
前经丁景老引介,蒙俯允亲见 贵馆珍藏陈独秀著《小学识字教本》。以此为据,与坊间巴蜀书社版本相核对后,始得以完成拙稿《陈独秀原著“小学识字教本”不应被删改》一文,现已在《世纪书窗》上发表。饮水思源,曷胜感激!该期刊物编辑部当已寄至贵馆,现复印拙稿一份奉上,尚恳 斧正为感!专此 即颂
大安!
吴孟明(“仲甫后裔”印)
展开剩余82%信末并未署日期,2001年5月20日是我的收信日。信中的“丁景老”即著名出版家、文史研究家、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社长丁景唐(1920-2017)先生。丁先生是前辈加师长,历来为我所敬重。我在鲁迅纪念馆工作多年,一直受到他的提点。1999年,我主持改扩建的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后,还在馆内的“朝华文库”二库中设置了“丁景唐专库”,收藏他的藏书等。吴孟明信中谈到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是我馆的藏品。信上的落款很有意思:在署名后面加盖了一个“仲甫后裔”印章,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陈独秀的这本书,怎么会由我馆收藏的呢?——这件油印本原为北大教授魏建功所藏。陈独秀在“小学”即文字学方面,有很深厚的研究功力,在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时候,有人说陈独秀没有什么专业,蔡元培就明确地说:陈独秀在小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陈独秀一直在文字学方面下功夫。虽然因为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没能写完他的文字学大作,但他是很重视的,直到1940年在四川江津卜居时完成了《小学识字教本》后,交给国立编译馆去出版。编译馆是想出版的,还预支了2万元稿费。但是当时规定这类书需要教育部审查,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却认为“小学”容易跟学校的低年级认字课本混淆,所以批示改题,但是陈独秀坚决不同意改题,说:“‘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断不能改。”这样,书就没法出版了。于是他找人油印了50份,分赠友人和弟子,魏建功和台静农都是帮陈独秀操办油印的人员,因此魏建功自己也保存了一份印本。早年毕业于北大的魏建功1940年由西南联大转到在白沙的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他研究文字音韵学,对陈独秀研究的文字学颇为关注,因此得以参与了油印工作。而台静农早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肄业,这时候正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与魏建功等人受陈独秀之托担负油印《小学识字教本》之责,因而与这本书有了不解之缘。陈独秀曾对台静农说过自己的治学思路:“过去研究文字的人,都拘泥于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文字学学说,前人理论也有许多谬误,已不适于时代。我有责任创作一部典籍,赋予文字学以全新面貌。”这表明了他对这部书是颇为用心,也颇为自信的。
但此书从此被束之高阁。1942年陈独秀去世,出版更加无望。直到1971年由梁实秋主持在台湾出版,改题为“文字新诠”,还把陈独秀的名字也隐去了。在大陆则直到1995年才由巴蜀书社出版别人整理手抄的影印本。1980年魏建功先生去世后,他所藏的油印本就由台静农先生保存。1990年台静农去世后,遗物中留有这份油印本。由于魏建功和台静农都是鲁迅弟子,所以台静农遗嘱这件印本及其它一些遗物要捐赠给鲁迅纪念机构。
此前,1980年代末期,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先生赴台看望台静农先生,那时候台老已经病重。陈漱渝带去一个老朋友的口信:希望台老及早把有些收藏品交给鲁迅纪念研究机构收藏。这位老朋友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李霁野教授。他是1925年与台静农同时加入鲁迅先生发起的未名社的成员,与台老感情深笃。当时台老还收藏着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记录稿。但台老当时病重,不及整理,就于1990年逝世,他的家属谨记台老的遗嘱,把台老的一些收藏品整合在一起,后来淡江大学教授施淑到美国时,就托她带回了台湾。正巧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到台湾访亲友,施淑教授便交给他一个纸箱,托他带回转交李霁野先生,其中就有这件油印本。陈漱渝先生带回北京,又到天津将纸箱交给李霁野先生,李霁野先生随即将其中物品分为两份,一份交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一份交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仍由陈漱渝先生带回北京,把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那份交给馆内,又把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那份托人转交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我馆的文物藏品登记册记载,是华东师大的陈子善教授交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得到这个捐赠信息时还多少有些意外的印象,因为我馆以往跟台静农先生或其家属并无联系。后来这本油印本被评为三级文物。
吴孟明先生得知我馆得到这件藏品后,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原社长丁景唐先生介绍,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找我,要求提看这个油印本。他是陈独秀家族后人,我们自然满足他的要求。我不记得是否复印给了他或者让他拍了照片。从他的来信看,应该是提供给他了,因为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已经把油印本与坊间的巴蜀书社版《小学识字教本》做了仔细核对。该书篇幅达四十多万字,这么大篇幅的印本,是不可能在来访我馆的短时间内核对完成的。
吴孟明先生回去后,经过仔细核对,写成了《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不应被删改》一文,发表于《世纪书窗》2001年第二期,文中详细列举了被不当删改的例子。吴孟明先生来我馆查阅那个油印本,似乎目的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现在文章写成,也发表了,所以来信致谢,还附上了他文章的复印件,可说是化解了他的一个心结。
吴孟明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插入了一封陈独秀致台静农的信,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台静农的嘱托和信任。信很简单,只有短短几句话:
静农兄:
拙稿如能真付印,望即就近在白沙石印,万勿木刻,书名亦望勿改!此祝
健康。
弟独秀启
七月十三日
这封信应该是1941年的个人炒股如何加杠杆控股,因为次年陈独秀就去世了。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的两点意见十分执著:一是就在白沙当地石印,决不能用木刻;二是书名不能改。这书饱含他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所以他对陈立夫要求他改书名非常恼火,宁愿不出,退回预支的稿费,也不改书名。这也就是真正的陈独秀性格。也正是因为这样,这部书在陈独秀在世时注定是出不成的,甚至连他希望的石印本也没能出,只能油印。吴孟明先生作为仲甫后裔,自然理解他的想法,因此为坊间印本有舛误而生心结,必欲为陈独秀的著作保存原汁原味,为原著被擅自删改讨要说法,这份苦心也是能够理解的。
发布于:上海市